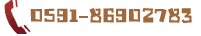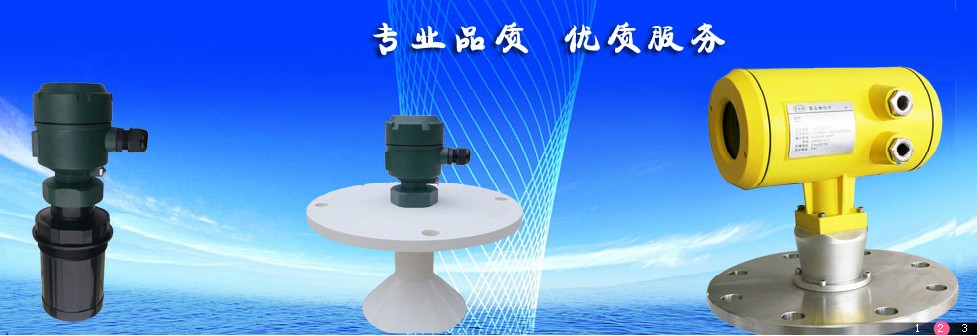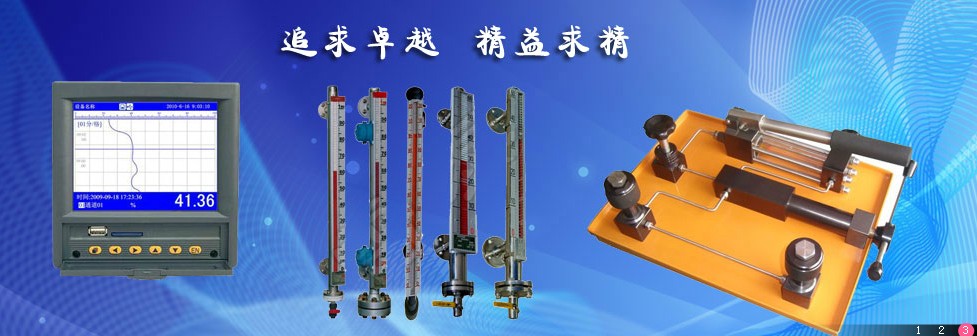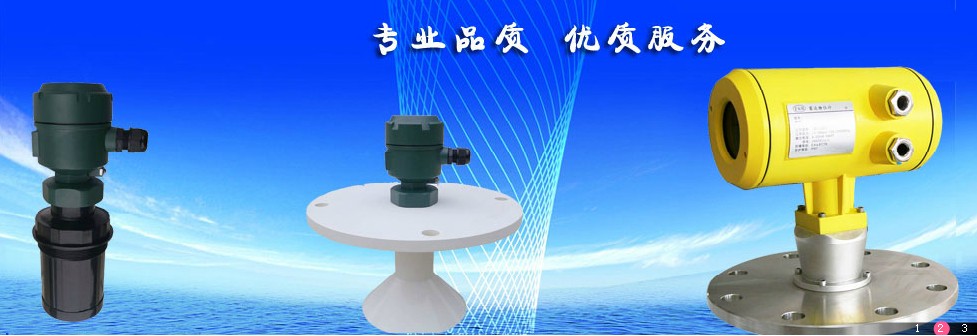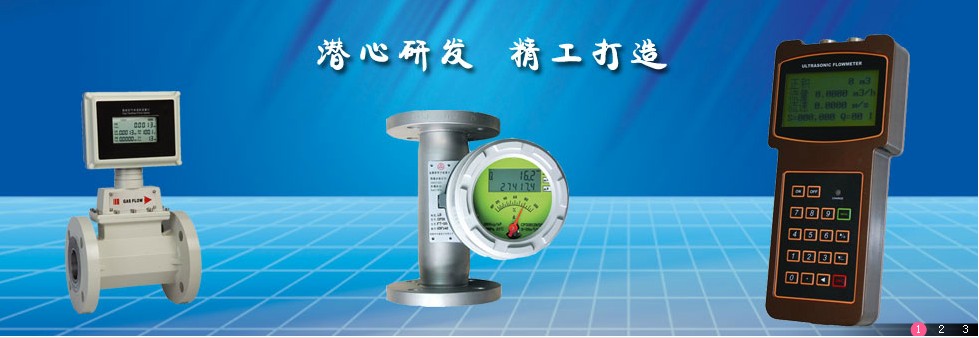“琉璃之路”与朝鲜半岛、日本出土的玻璃器
点击次数:2019-11-13 17:58:10【打印】【关闭】
古代东方与西方的交往和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展,不仅有商品货物的交换和传播,也有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不仅有绿洲道,还有草原道、南海道甚至海东道。这条途径不单单是“丝绸之路”,还是“香药之路”“珠宝之路”和“琉璃之路”[1]。中国之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出土了大量西方风格的玻璃器,展现了三地紧密的联系和“琉璃之路”向东的延伸。
一 朝鲜半岛的古代玻璃器
据推测,玻璃制作技术是在汉代同铁器制作技术一起传入朝鲜半岛的。从多个遗址中出土有模具这一点来看,当时已能自行生产[2],但出土品主要是勾珠、管饰等玻璃制品。本文所谓玻璃器主要指玻璃容器,大多属于三国时代(公元4-7世纪)。自1921年对金冠冢开始进行调查至近年的出土发现,迄今在朝鲜半岛发现的玻璃容器约有30件,大多集中在韩国庆州及其周边地区[3]。兹择要述之。
庆州市内,玻璃器主要出土于天马冢,皇南大冢南坟、北坟等大规模的双圆坟中,在金冠冢、金铃冢等小规模的积石冢中也有出土发现。庆州盆地外主要有安康邑安溪里4号墓和庆尚南道陕川郡玉田古墓群1号墓[4]。
皇南大冢(旧称98号坟)属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新罗墓葬,可分为南坟和北坟,年代在5世纪中晚期。北坟出土浅绿色磨饰玻璃碗、彩色高足杯、蓝色玻璃杯各1件,另有2件残损的玻璃杯。南坟出土了浅绿色凤首壶、浅绿色波纹玻璃杯、蓝色玻璃碗各1件,浅绿色玻璃杯2件,还有2件器物残损。一些玻璃容器的造型和装饰可与在中国、日本发现的同时代器物相对照。
图一磨饰玻璃碗
1.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北坟出土2.伊朗吉兰出土3.中国镇江句容出土4.中国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
图二波纹玻璃杯
1.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南坟出土2.韩国庆州瑞凤冢出土3.中国河北景县祖氏墓出土
北坟出土的磨饰玻璃碗,高6厘米、口径10.5厘米,浅绿色透明,敞口,圜底,通体有6排凹球面磨饰,底部也有1个较大的圆形凹球面(图一:1)。凹球面磨饰玻璃碗在伊朗高原出土最多(图一:2),流行时间最长,在中国、日本也有较多发现,如中国江苏镇江句容六朝墓(图一:3)[5]和山西大同南郊107号墓(图一:4)[6]出土的玻璃碗,日本安闲陵出土玻璃碗(图九)[7]和正仓院藏玻璃碗(图一〇)[8]。以上这些玻璃碗年代大体相当,装饰技法基本相同,只是口、颈部表现不同,可归为同一类型。显然,它们的年代和制造地点应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属于波斯萨珊王朝的制品[9]。
南坟出土的波纹玻璃杯高12.8厘米、口径9.5厘米,颈部有1条波纹,腹部有3条波纹相互衔接形成网目纹(图二:1),与庆州瑞凤冢(图二:2)[10]、河北景县祖氏墓出土波纹碗(图二:3)[11]风格相似。黑海北岸5世纪的罗马遗址曾经出土过许多饰有波浪纹或网纹的玻璃器残片。中国和朝鲜半岛出土的这种饰有波浪纹的玻璃器,可能来自罗马时期的黑海北岸[12]。
南坟出土的凤首玻璃瓶,高25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6.5厘米,细颈,鼓腹,圈足较高,壶把上端在口部(图三)。这种器形的器物在中亚、西亚可以经常见到,罗马到伊斯兰时代都有发现,传至东方后,被称为胡瓶。发现的这类器物多为金银器,还有陶器。中国唐代的陶瓷器、塑像和壁画中多有带把壶,就是模仿西方器物特别是金银器。以前认为这件玻璃器的产地可能是在中东或北非,属于罗马玻璃[13]。但最近有研究认为,这是一件出土于地中海东岸的萨珊玻璃器[14]。
饰有蓝色斑点的玻璃碗在金铃冢和玉田古坟均有出土。金铃冢发掘于1924年,出土2件玻璃杯。其中一件浅绿色透明,敞口,腹部有2周斑点,上周11个,下周10个,高6.9厘米、口径10.5厘米(图四)。而玉田古坟群位于距庆州市西部100公里的庆州南道陕川,其中1号墓的年代被推测为5世纪的后半期。玉田1号墓出土的玻璃碗与金铃冢出土的蓝色斑点纹碗酷似,腹部配饰两列深蓝色的玻璃斑点,高7.1厘米、口径9.7厘米。德国科隆地区、黑海附近的乌克兰及俄罗斯地区都曾发现饰有蓝色或褐色斑点的玻璃器,其中科隆地区出土玻璃器的时代约在公元3-4世纪,乌克兰及俄罗斯地区出土的玻璃器年代约在公元4-5世纪,金铃冢和玉田古坟1号墓出土的斑点纹玻璃杯可能来自以上地区[15],属罗马玻璃。
天马冢出土2件玻璃杯,其中蓝玻璃杯上部为竖线纹,下部为吹制的龟甲纹(图五:1),器形与康宁博物馆藏玻璃杯(图五:2)[16]和南京下关区象山7号墓出土玻璃杯(图五:3)相似[17]。这种玻璃杯在德国科隆地区和叙利亚地区都能找到类似产品[18],其上部纹饰则与印度本治理出土的罗马玻璃残片一致[19],被认为是公元4世纪的罗马玻璃制品。
图三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南坟出土凤首玻璃瓶
图四韩国庆州金铃冢斑点纹玻璃杯
图五
1.韩国庆州天马冢出土蓝玻璃杯2.美国康宁博物馆藏玻璃杯3.中国南京下关区象山7号墓出土玻璃杯
图六
1.韩国瑞凤冢蓝玻璃碗2.中国河北景县封魔奴墓玻璃碗
瑞凤冢出土蓝色玻璃碗和波浪纹玻璃杯各一件,蓝色玻璃碗高4.7厘米、口径10.4厘米,圆唇,腹部有一道细阳弦纹,矮圈足(图六:1)。瑞凤冢玻璃碗与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图六:2)器形和成分相似,属于钠钙玻璃,还有一定量的锡,均属罗马玻璃[20]。
朝鲜半岛的寺院塔基也出土玻璃器。1959年,韩国庆尚北道漆谷郡松林寺维修时,在统一新罗时期(约668-901年)五重塔的塔基内发现1件凸圈纹玻璃杯,高7厘米、口径8.4厘米,置于一个高约14.2厘米的金铜殿阁形舍利器内。玻璃杯口外侈,圆唇,圜底,淡绿色透明,外侧有3段12个环形贴饰。内放绿玻璃舍利瓶,高6.3厘米、腹径3.1厘米。细长颈,鼓腹,上有宝珠形玻璃栓(图七)。玻璃瓶含铅量较高,年代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可能为中国制品[21]。据研究,凸环纹玻璃器为中亚玻璃,主要流行于公元7世纪[22]。松林寺凸圈纹玻璃杯同正仓院蓝玻璃杯相似,年代应为公元7世纪[23]。另有庆北奉化惊捷寺塔舍利瓶、庆北西洞里舍利瓶、庆州皇龙寺址舍利瓶等,年代多为公元9世纪,但来源尚不能确定[24]。
图七韩国庆州松林寺玻璃杯和瓶
此外,还有突起纹玻璃杯、水注、葫芦瓶等玻璃器皿在朝鲜半岛出土。它们的年代较晚,突起纹杯和水注出土在黄海道延白郡,年代在公元8-9世纪,而葫芦瓶属于11-12世纪的玻璃制品[25]。
二 日本的古代玻璃器
日本处于丝绸之路东端,主要通过朝鲜半岛和中国与中亚、地中海地区、北非以及欧洲联系起来。从现有资料看,日本列岛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弥生时代中期开始使用玻璃。最早的玻璃集中出土在北九州福冈县,包括很多单色的玻璃珠和玻璃管,经化学分析是与中国汉代玻璃一样的铅钡玻璃。从古坟时代(3世纪中期以后)中期开始,玻璃容器被随葬于古墓中,最早发现于新沢千冢126号墓。
日本橿原新沢千冢126号墓出土玻璃碗,淡绿色透明,颈微收,口外侈,圜底球腹,腹部5排底部3排圆形磨饰。高约6.8厘米、口径7.8厘米、壁厚1.5毫米。无模吹制而成,砂轮打出圆形纹饰(图八:1)。同墓还出土一件深蓝色玻璃盘,器皿是作为盏托使用的(图八:2)。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此墓年代被定为公元5世纪。此玻璃碗属于萨珊玻璃,但造型上仍与罗马玻璃一脉相承[26]。
图八日本新沢千冢1 2 6 号墓出土玻璃器
1.磨饰玻璃碗2.蓝色玻璃盘
图九日本安闲天皇陵出土的玻璃碗
图一〇日本正仓院藏玻璃碗
类似的托盏套件1873年出土于大阪府堺市大仙古坟。这座古坟被认为是日本仁德天皇的陵墓,故发掘后器物再次埋葬于石棺中。据当时所临摹的绘图,此套托盏与新沢千冢的盏碗大小相似,形状一致[27]。
图一一日本冲之岛祭祀遗址出土玻璃残片
安闲天皇陵墓的古坟在18世纪出土有磨饰玻璃碗,高8.6厘米、口径12厘米。浅褐色透明,口微敛,圜底球腹,腹部有5排圆形纹饰,底部也磨有1个直径较大的圆形凹球面(图九)。如前所述,与其同器形、同大小的雕花玻璃容器在正仓院也有收藏(图一〇)。此两者器形、大小相同,雕花的段数、大小、数量均一致,可能为同一时期的萨珊玻璃器,年代约为公元6世纪。
福冈县宗像冲之岛祭祀遗址素有“海上正仓院”之称,发现祭祀遗址达23处之多。其中8号遗迹中先后出土了2块玻璃残片(图一一),同属一圆形凸起装饰玻璃碗的的腹部(图一二)[28]。玻璃残片淡绿色透明,内含气泡,壁厚3毫米,在外壁有一个凸起的圆形纹饰,圆饰呈凹球面,直径2.8厘米,与北周李贤墓出土的萨珊玻璃碗(图一三)的纹饰、工艺相同,年代也相同[29]。从8号遗迹的其它出土品来看,推测其在6世纪后期是作为祭祀用品而使用的。
此外,在京都市的上贺茂神社出土有玻璃容器的残片,长约6厘米、宽约4.2厘米,白色不透明,外表有凸起的同心圆纹饰,为凸起装饰玻璃碗的腹部残片[30]。根据残片的弧度及纹饰,可以复原为一件圜底碗,碗腹部的同心圆也是砂轮打磨抛光形成,但工艺比冲之岛工艺更为复杂,至今在东亚还未发现有同器形的碗。
7世纪后期以后,作为佛教寺院的舍利容器及显贵人士的骨藏器的玻璃容器,在日本列岛也有生产[31]。但也有从唐朝输入至日本的玻璃容器,最为人所知的是唐招提寺的舍利瓶。该白琉璃舍利瓶高9.2厘米,隆肩,肩宽11厘米,斜收腹,底内凹(图一四)。传这件琉璃瓶是鉴真和尚从中国带去日本的,年代应在8世纪[32]。该瓶与河北定州净志寺塔基出土的细颈瓶极为相似[33](图一五),且同属钠钙玻璃,并含一定的钾。一般认为这两件玻璃瓶来源相同,可能是伊朗高原上伊斯兰玻璃的早期产品[34]。
滋贺县崇福寺塔塔心出土舍利壶,高3厘米,放置在莲瓣形金箔座上,从内到外依次套放在金制外箱、银质外箱、铜质外箱内(图一六)。琉璃壶深绿色球形,较为厚重,上有金盖,内置无色透明粟粒大小的舍利3粒。年代为公元7世纪,与中国临潼庆山寺、扶风法门寺,韩国庆州松林寺塔基出土情况相似[35]。说明了当时的文化交流。
图一二日本冲之岛祭祀遗址玻璃残片复原图
图一三中国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玻璃碗
图一四日本唐招提寺琉璃瓶
图一五中国河北定州静志寺细颈瓶
图一六日本滋贺县崇福寺塔塔心出土舍利壶
图一七日本京都竜吟庵大明国师像内玻璃瓶
图一八日本奈良於美阿志神社出土玻璃瓶
图一九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藏玻璃器
1.蓝玻璃高足杯2.紫玻璃壶3.白玻璃瓶4.十二曲绿玻璃杯5.玻璃高杯
另外,在京都竜吟庵大明国师像内藏有舍利容器,其中有绿玻璃舍利容器瓶、金制舍利容器,木质五轮塔等(图一七)。其中绿琉璃瓶高2.7厘米,年代在13世纪[36]。
奈良於美阿志神社内原道兴寺石塔基内出土盛舍利的小口玻璃瓶(图一八)[37],与中国河南密县法海寺出土的宝珠形小瓶极为类似,该瓶贮于大陆烧制的青白釉瓷罐和褐釉四耳罐中,可推知舍利瓶来自中国[38]。
图二〇日本奈良法隆寺金堂壁画中玻璃器
在日本,保存玻璃器皿最集中的莫过于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计有蓝色玻璃高足杯、淡褐色玻璃高杯、白玻璃瓶、紫玻璃壶、十二曲绿玻璃长杯和白玻璃碗等(图一九)。此外,还有玻璃鱼饰、玻璃棋子以及大量的玻璃珠和玻璃原料,色泽多样,包括褐、绿、青、白等等。这批器物保存完整、种类多样,对研究南北朝、隋唐时代玻璃器物的制作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弥足珍贵。学者对此已有详论,兹不赘述[39]。
随着佛教艺术的东传,日本佛教绘画中也出现玻璃器的形象。日本法隆寺金堂保存着公元7世纪的壁画[40],包括外殿四面大壁上的《四方四佛净土图》、八面小壁上的《菩萨图》等等。其中第一号壁画描绘的是释迦净土。右面胁侍菩萨持玻璃盘,左面的胁侍菩萨持瓶[41]。玻璃盘浅腹、圜底、侈口,腹径略小于手长(图二〇)。
日本和朝鲜半岛出土的这些玻璃器,均出现在寺院珍藏、皇室大墓和神社的祭祀遗址,说明这些玻璃器在当时是罕见的珍贵之物。
三“琉璃之路”向东的延伸
考古学上的东西文化交流,应该是从欧洲的地中海沿岸起,通过中国腹地,一直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中国和日本之间,海面宽阔,直接的交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很大的限制,故日本在吸取大陆文化的历史过程中,朝鲜一直起着窗口和桥梁的作用[42],从而在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形成一个多向的文化交流网络。
春秋晚期,西亚的玻璃珠饰以中亚游牧民族为中介,进口到中国中原地区,刺激了中国玻璃业的诞生。战国时期,中国利用本地原料,生产独特的铅钡玻璃,并在西汉时期东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43]。日本绳纹时代出土过勾珠及生产勾珠的范[44],这些勾珠无疑是日本当地制造的,经检验都是铅玻璃。正仓院还保存了公元7世纪玻璃珠子的配方,记载了需用大量的氧化铅[45]。显示出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早期玻璃器的密切关系。
许多在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玻璃容器,都可以很容易地在西方找到相似的器物。新疆、甘肃等地发现大量玻璃器,说明两京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也应是西方玻璃器传入的主要途径。但北魏前期都城平城逐渐兴起,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可以不必绕河西走廊,直接从伊吾向东,过西海郡,横穿蒙古草原达平城,向东可到营州、辽东和朝鲜半岛,渡海至日本。从公元4世纪开始,至公元11世纪,这条横贯中国北部草原的交通路线,在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交流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高句丽和百济虽然与中国交往更加频繁,但尚未有玻璃容器出土,无法判断新罗的玻璃容器是由陆路经高句丽无间断性传入[46]。故新罗与南朝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绕到朝鲜半岛东南部海岸或是直接从朝鲜半岛南海岸到达长江口后由陆路到达目的地。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 汉唐时期达到了高潮,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条主要的文化线路, 即北方经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的陆路、从山东半岛出海的海路以及南方从长江口出海的海路。”[47]而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时代又决定了其交往路线表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48]。
中国和朝鲜各国之间的官方贸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贡使贸易。朝鲜半岛的百济与中国南北朝政权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曾5次遣使来访北朝诸国,33次来访东晋和南朝诸国[49]。唐朝时期,新罗以朝贡、献方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共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以册封、答谢等名义共向新罗派出使节126次[50]。新罗使团每次赴唐,都带来许多物品,进献唐朝皇帝,唐朝皇帝在其归国时也向新罗国王和王室回赠礼品。
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流也十分紧密。新罗景德王十一年(752年),新罗王子金泰廉一行访问日本,带去了大量的香药、药材、颜料、金属品和日常随身用具等,包括唐、南海、西亚等地的转手货物和新罗的特产。表明新罗人经由唐朝或部分通过直接贸易而获得了欧亚各地的产品[51]。这一时期新罗的使团同时具有外交使节和商人的双重性格,想通过朝贡的形式获取商贸利益,魏晋时期朝鲜与日本的交往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时的日本使节、僧侣、留学生、商人也直接从唐朝转送玻璃器回国。日本入唐求法僧空海,于日本大同元年(806年)十月十二日,将其从唐朝携归的译经、宝物,一并记入《御请耒目录》中,其中有碧0) 璃供养碗二口、白0) 璃供养碗一口、绀0) 璃箸一具,注明系青龙寺惠果和尚所付;大唐大中十一年十月,日本求法僧圆珍曾上《入唐求法目录》,其中载:“琉璃瓶子一口”,是日本僧田圆觉从广州寄送的;另一只“0) 璃瓶子”,则是日本国商人李觉英、陈太信等附送,将回本国永充供养的。这种传播可提前到很早的时期,宿白先生认为日本福冈须玖冈本和三云两处弥生中期翁棺中发现的玻璃璧,大约即是公元前后由大陆东传的[52]。
从西方到东方,出土了大量的玻璃器物,可以说玻璃器成了当时的一种全球化的产品,也是当时东西方之间丝绸之路贸易最清晰的证据之一。朝鲜半岛和日本出土的玻璃器,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也显示出“琉璃之路”向东的延伸。